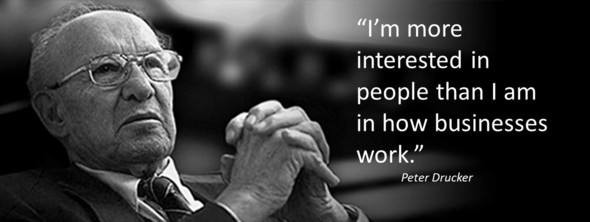

德鲁克谈真正的老师
2015-04-07 文/彼得·德鲁克
【王家骢评语:这是我几年前转发的文章,今天看起来依然很很合时宜。我从事管理培训工作十几年,对于德鲁克所说的“真正的老师”深有体会。没有不称职的学生,只有不称职的老师。作为一名教师,关键不在于自己讲的多精彩,而在于是否能够让学生听明白。老师的焦点应该在学员身上。老师的工作是让学生学会使用知识。这也是我强调自己是“管普工作者”的初衷,要用学员能够听懂的方式传授管理的知识,让他们能够在工作应用这些知识。】
文/彼得·德鲁克
我一直在寻找真正的老师。我不遗余力地在探访他们的身影,观察他们教学的方式,并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。我一听说谁是“大师级”的老师,就设法溜进这位老师的课堂上旁听、观看。若是不得其门而入,也设法问学生,看这位老师是怎么教的,他成功的地方在哪儿。
因此,多年来,“教学观摩”一直是我最大的喜好。好比看精彩的运动比赛,绝无冷场。至今,这种观察的兴味仍不减当年。
有一件事,在我很小的时候知道了,那就是学生总是可以辨认出老师的好坏。有的只是二流老师,但是舌灿莲花,机智幽默,因此留给学生至为深刻的印象;有些则是颇负盛名的学者,但是不算是特 别好的老师。但是,学生总可以识别出一流老师。第一流的老师并不经常广受欢迎,事实上,大受学生欢迎的老师,并不一定能对学生造成冲击力。但是,如果学生谈到上某位老师的课:“我们学到很多。”这样的话可以信赖,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样才是好老师。
我还发现,“老师”实在是不易定义。或者说,“教学得力的因素何在?”这样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。我从未看过做法完全相同的两个老师,每个老师都有其独特的表现方式。使一个老师成为第一流的方法,似乎对另一个老师来说完全没用,而另一个老师或许也不会采用这种方式。这个现象真令人困惑,至今我仍大惑不解。
有些老师是不用语言的,就像苏菲老师。施纳贝尔亦然。然而,同一时代还有两位卓越的音乐老师却很爱说话。过去50年来,在美国最厉害的钢琴老师就是列维涅,她上课老是说个不停,很少做示范;在老年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声乐老师的奥地利女高音勒曼也是。
有的老师比较会教高深的课程,有的老师则较适合教初学者。20世纪两位卓越的物理学家也是伟大的老师:他们是哥本哈根的玻尔1885-1962,丹麦物理学家,量子力学的先驱,192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)和费米(1901-1954,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,193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,1939年赴美,1942年主持建立世界上第一座原子核反应堆)。费米晚年时就在芝加哥教书,但是玻尔只教天才学生。我听物理系的学生说,即使是最有天分的学生,也发现玻尔几乎让人无法理解。玻尔在上课前亦下了很多的准备功夫,然而学生却不能从他的授课和主持的学术研讨会得到什么。现代物理的第二代大师,从海森伯(1901-1976,德国物理学家,创立量子力学,193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)到薛定谔(1887-1961,奥地利物理学家,1933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),乃至奥本海默(1904-1967,美国物理学家),在研究所深造时都接受过玻尔的指导,他们都把自己能成为科学家归功于玻尔。相形之下,费米比较会教大学部的学生,特别是新生、不准备踏入物理这个领域的,或是从来没有修过物理的学生。现代舞大师玛莎·格雷厄姆也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,不管是初学者或是卓然有成的舞者,她都教得很好,而且用的是同一套教学法。
有些老师则比较会上大班课,在众多学生的面前讲课。富勒(1895-1983,美国建筑师、工程师、发明家、哲学家,也是诗人,被誉为20世纪下半叶最有创见的思想家)的课堂上足足有2000个学生,大家可以连续7个小时目瞪口呆地听他讲课。有的老师则在教小班课时,比较得心应手,女高音勒曼就是最好的例子。还有些老师像马克·霍普金斯(1802-1887,美国教育家、道德哲学家)则在一对一教学时,教得最好。有一句老话说,最好的学校就是要“霍普金斯站一端,一个学生在另一头”。然而,我本人还未见识过这样的老师。好老师就像是节目主持人,他们需要观众。有的老师是用书写的方式教学,而不是用口语。第二次大战的美国将领马歇尔就是一例,通用汽车总裁斯隆也是。斯隆的书信也汇集在他再版的书《我在通用的日子》当中;此书也是教学的大师之作、当然,教给我们基督教传统的老师圣保罗,也是最伟大的老师,他是以书信教导后人的。
表演者的能力和教师的才能似乎没有什么相关,研究学同与教学或是技巧与教学之间也没有关联。在欧洲传统中的大画家只有了托列的学生很多,但是没有一个学生可以达到二流画家的水准。格列柯例外,所有大画家几乎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平庸画家教出来的。尽管奥本海默是卓越的管理人才,却未能脐身于相对论、量子物理和原子物理的伟人之列,但他却是个天才老师,激发年轻一代美国物理学家的创造力,使他们发光发热。像我这样对物理一无所知的人,聆听他在普林斯顿的讲座,觉得眼前像是浮现出了壮丽的高山、大海。海顿、莫扎特和贝多芬在维也纳时,也受教于一位伟大的老师——迪亚贝利,而他留给后世的不过是些枯燥无味的手指练习曲。再下一代的名师并不是舒曼、勃拉姆斯、瓦格纳,也非李斯特、柏辽兹,这些只能算是不错的老师,真正的名师是舒曼的遗孀克拉拉,她才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钢琴教师。
通过“教学观摩”,我很早就下结论道:老师没有一定的种类,也没有完全正确的教学法——教学就像一种天赋,像贝多芬、卢本斯和爱因斯坦等那些与生俱来的奇才;教学是个人特质,和技巧和练习无关。
多年后,我又发现另一种老师。更正确的说法该是,他们会激发学生学习。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,并非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天赋,而是凭借着一种方法来导引学生学习,正如我小学四年级的老师埃尔莎小姐。他们发掘每个学生的长处,并为他们立下近期与远程的目标,让他们更上一层楼。然后,再针对每个学生的弱点下对策,使他们在发挥自己长处时,不至于受到弱处的牵制。这些老师并使学生从自己的表现中得到相当的回馈,进而培养自律、自我引导的能力。这样的老师多半会鼓励学生,而不是一味地批评,但是他们也不会滥用赞美的言辞,以不至失去刺激的效果。他们认为该给学生的主要奖励就是满足和成就感。他们并没有“教”学生,而是为学生设计出学习的方法。因为总是采取一对一的方式,这种教学法几乎适用于每一个学生。因此,教学并不是指某个学科的知识,或是所谓“沟通技巧”,而是一种特质。对苏菲小姐那样的老师而言,教书和人格特质有关;至于埃尔莎小姐,教学则是一种方法。
因此,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老师:一是天赋型的,另一则为学生设计学习课程,以方法为主的。教书是一种天赋才能,天生的老师可自我改进并成为更好的老师;以方法为主的老师则有一套几乎人人适用的学习法。事实上,天生的老师再运用一点教学法,就可以成为伟大的老师,也可成为无所不能的名师,不管是在大讲堂上课、小组教学、教初学者或是指点已相当精进的学生都能愉快胜任。
苏菲小姐就有天生老师的魅力,而埃尔莎小姐则有自己的一套方法;苏菲小姐让学生豁然开悟,埃尔莎小姐则教给我们技能;苏菲小姐把梦想传达给我们,而埃尔莎小姐导引我们学习——苏菲小姐是教师,而埃尔莎小姐则是利用教学法的人。这种区分并不会使古希腊的先哲,如苏格拉底大为意外。传统上,苏格拉底亦被称为伟大的老师。对此称呼,他本人应该不以为忤。但是,他从来就没有说过自己是个老师,事实上他也是一个利用教学法、引导学生学习的人。
苏格拉底的方法并不是“教的方法”,而是“学的方式”,一种特别设计的学习法。苏格拉底对诡辩学派的批评就是因为他们太强调教的一方,并认为老师教的是“学科”。苏格拉底则觉得这种看法没有意义,他以为:老师教的不是“学科”,而是“学习方法”,学生从而学到该学科的知识。“学”是有成果的,“教”则是虚假的;这种看法使他成为阿波罗神话中“希腊最有智慧的人”。
然而,过去两千年来,主张教学是可教的诡辩学派一直是主流。他们最后的大胜利就是美国高等教育盲目的信条,认为博士学位或是对某一学科的深究就是教学的先决条件。还好,诡辩学派所能主导的,也只有西方。其他文化中的老师并不像西方诡辩学派所说的。印度文里的老师就是“宗师”(guru),亦即灵性的导师,这些“古鲁”是天生的,而不是后天学成的;他的权威不是出自对某一个大学学科的研究,而是由精神而来。同样地,日本人所称的“先生”(Sensei)就有“大师”的意思,也不是单指老师。但在西方传统中,我们却把教书视为一种技巧而忘却苏格拉底的话:“教书”是天赋,“学习”则为一种技巧。
直到20世纪,我们才重新发现苏格拉底对“教”与“学”的定义。过去100年来,由于我们比以前更认真地研究“学习”这个课题,所以才能重新体认苏格拉底的话。我们发现,学习是深植于每一个人身上的,人类以及所有的生物都是照着一定方法学习的“学习体”。研究了一整个世纪后,我们对学习的认识,还比不上埃尔莎小姐,但是我们很清楚,她的所知所行都是对的,而且适用于每一个人。
从苏格拉底的时代至今,两千年来,我们一直在辩论“教”与“学”到底是属于“认知的”还是“行为的”范畴。这真是一场无谓的战争。其实,两者皆是,也是另一种东西,那就是热情。天生的老师一开始便满怀热情,而善于利用教学法的老师在学生有所领悟时,而获致热情;学生脸上那心领神会的微笑比起任何药物或麻醉品更令人上瘾。老师自己都教得烦闷无趣的话,教室有如被瘟疫肆虐一般,不管是教书或学习都会受到相当大的阻碍——这种病症,只有“热情”能够解救。教与学好比是柏拉图式的爱(PlatonicEros),也就是柏拉图《会饮篇》(Sympasium)中谈到的爱;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匹尊贵的柏拉图飞马,从教或学当中,才能找到伴侣。对天生的教师而言,热情就在他们身上;对利用教学法的老师来说,则可在学生的身上看到热情。但是,不管教与学,都是热情,一种是天生就有的热情者,另一种则是陶醉于热情而不可自拔者。
天生的教师和利用教学法的老师又有一个相同点:他们都非常负责。
对真正的老师而言,没有所谓的坏学生、笨学生,或是懒学生之别,只有好老师和差劲的老师之分。
(摘自《旁观者》,彼得·德鲁克/著)

Copyright ©2019-2020 苏州智健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苏ICP备19033803号